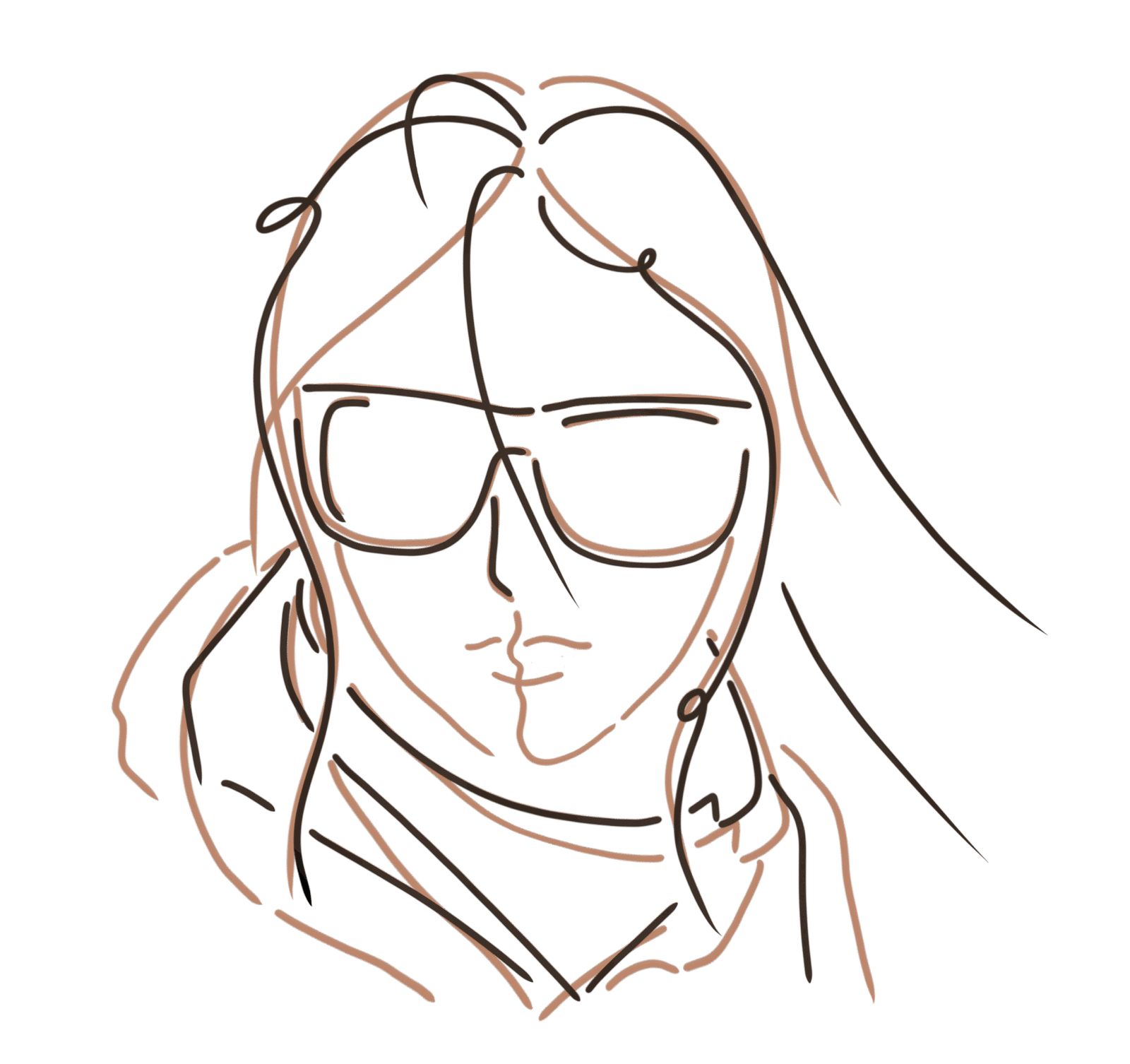西藏
故事发生的地方叫做当惹雍错。
“当惹”是古象雄语中“湖”的意思,而“雍错”在藏语中是“碧玉般的湖”,也可说是“圣湖”。我本以为以“错”来称呼西藏所有的湖泊就可以逃脱翻译过程中语义重复的诅咒,可最终还是在此折戟——也许这世上所有的山都只应叫做山,而所有的湖都只应叫做湖,因为那第一个见到并命名它们的人很可能终其一生也没再见过其他的山与湖。
西藏以其高原风光和宗教文化闻名,然而我这次是慕前者之名而来,直到行至才被后者所惊叹,因此只得临时抱佛脚,到了坐在湖畔的石头上才想起该考究下它的故事,就好像那湖泊与雪山会突然张口对我提问,若是不能答出一二便会被勒令离开。得益于此,到了如今落笔的时候我还是能卖弄几分,毕竟若说景色,那绝不是用文字所能描述的。
当惹雍错是苯教圣湖,紧邻苯教神山达果雪山,是中象雄文明的核心区域。时至今日,湖畔的文布南村仍然是一个信奉苯教的村庄。在西藏之行的第九天,我们决定在此留宿。不过,不过,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这个夜晚却并不安宁。
当然,在夜晚之前还有白天,我们还是按顺序讲起。我首先要讲到的其实是扎日南木错,就从颜色开始!——但提到颜色,我又不得不先讲讲西藏的其他湖泊们。高原湖泊的特点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蓝”,但它们的蓝是不同的,通常来讲,明亮的浅色湖泊会有些发绿,比如佩枯措;广阔的湖泊是深邃的海蓝色,比如色林错和纳木错;阴天的羊卓雍错是深灰蓝色,傍晚时逆光的玛旁雍错和拉昂错是白茫茫的一片——也许也是蓝色,只是我实在睁不开眼。
当天上午,我们先去看了扎日南木错,这是我此行最期待也是最终最喜欢的湖泊。扎日南木错的意思是“至尊湖”,可惜我没能带着一张至尊披萨来坐在湖边吃。它有着不可思议的亮蓝色,当我站在它身边时,我仿佛站在世界上最明亮的地方——只有光,没有影——可我却能睁开眼睛,或者说,我看的无比清楚:它是最好的、最纯净的,是这世界上笑得最快乐的人的牙齿和眼睛,是见过它的人的皮肤和心脏,是阳光,是歌声,是阳光下的雨水,是幸福者的眼泪!我想要为它而笑,为它扬起眉毛,为它起舞,为它忘记烦恼……
我走下山坡回到车里,远远地望着它,只有这样我才能思考——用我因为高反而不大清醒的大脑思考:它的海拔在高原湖中并不突出,可它却让我感到离地面如此远,远到忘记在人世间的生活是何年何月的事,我想是因为那蓝色,明亮的蓝色,清晰的蓝色,轻盈的蓝色,湖岸拖着我向上……它把我举起来了!我听到寂静无声,我抬手摸到了天空。
该走了,该走了,时间不早了,而我也莫名不贪恋这蓝色,我所看到的已经足够——即使平分给我生命的每一天。接下来是几个小时的野路,师傅骄傲地讲着这条无人知晓的捷径,去割草节的藏族村民向我们问路,爸爸在帮我找路边的狼和其他野生动物,而我被晃的昏昏欲睡——直到下午,我们终于看到了当惹雍错。
那是一种普通的蓝色……缄默的蓝色?但又是一种特殊的蓝色——最纯正的蓝,不偏暖或偏冷,不能称为明亮或深邃,只是蓝色,最浓郁的蓝色,蓝到几乎不透明,蓝到用手捧起的一汪水也是蓝色,蓝到即使闭上眼睛,用耳朵去听、用舌头去尝也是蓝色,蓝到几乎包含了所有颜色后仍是蓝色。我想大概是因为它见证过许多故事,最好的和最坏的,保守着许多秘密,最古老的和明天的,它被染成所有颜色,但所有颜色又都敌不过这蓝色,所以它变成了这样,像水粉颜料……或者蓝色的石灰水?总之,它似乎是这些湖泊中唯一有能力将世间万物都染成蓝色的。
好了,好了,继续向前走吧,别再说它的颜色了,这些美丽的宝石已经置换掉了我的双眼,我已经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临近傍晚,我们抵达了文布南村,在这样一片圣地,又遇上晴朗的天气,我该在晚上去湖边看星星,可惜酒店前台的藏族女孩警告我们这里有藏马熊出没,夜间最好不要出门,便只得作罢。
我们住在二楼,上楼后我便躺到床上,爸爸妈妈在房间进进出出。我的心跳的很快,我总有种冲动,想喊他们都留房间里,不要再出去了。
我不喜欢那个前台的女孩。
傍晚,我们走到电梯口,打算去顶楼看看有没有能拍星星的地方,电梯门开了,那个前台女孩正站在里面。我赶紧后退,看着她走了出去,我想询问哪里能拍星星,但我害怕和她说话。其实我是害怕她的眼睛,她的眼皮很薄,这似乎导致她的眼球离我太近了。我见过几次这种眼睛,野兽般的纯洁,和它们对视会让人迷失,你会误以为这样薄的眼皮藏不下什么秘密,便去看他们的眉毛和嘴唇,而等最终看到那双眼睛时才觉得:我应该先看看它们。
她跑到了楼道尽头,进了一个房间,像是去送东西的,就在我打算离开时,妈妈说要等她出来问问她。
根据女孩的指引,我们坐电梯到了三楼后从左侧的楼梯爬上了楼顶。楼顶分为左右两侧,形似哑铃,中间连接区域有两个阁楼和许多管道设备,右侧也有楼梯连通到三楼,但门是关着的。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正是日落,跳跃的金光显得喧闹,可湖水依旧沉默。爸爸掏出一堆相机和镜头拍照——他是永远都找不到合适的设备的,除非每个都用上。
我为了取东西上下天台几次。要想去天台,需要先走出房间,穿过一段能直接看到一楼大堂的连廊到达电梯口,坐电梯到三楼,再从左手边那个铺着白色瓷砖的楼梯上一层楼,穿过屋顶常开的防火门到达天台左侧,再穿过管道密布的哑铃杆,走过两个阁楼漆黑的门口,最终到达右侧天台。第二次上楼时,我开始没由来地害怕那个电梯,直到看到电梯口贴着的纸条,上面写着:“进入电梯前,请确认电梯已到达。”
我决定爬楼梯到天台。
可三楼到天台的走廊也让我感到不安,我不喜欢那些瓷砖,但这段路是绕不掉的。我总是盯着那些瓷砖看,尤其是墙壁上的,雪白的,崭新的,和这酒店颇具民族风格的墙纸格格不入的,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只是在楼道里越走越快,直到跑起来。最后一次上楼是日落时分,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楼顶晾晒的衣服突然被清空了,而他终于走了出来。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人,一个被困住的的灵魂呢?他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这里恐怕真的是地球的第三个极点,因为再找不到比这里更遥远的地方了,离所有可说的事物都如此遥远。我坐在车上穿过苍茫的恶地,像每次旅行时一样,可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车子停下,那我该如何翻过这高山,走过这荒原呢?
我喜欢打剧本杀,不过有日子没打了,所以来玩个推理游戏吧!客观地讲,电梯门口会出现那种标语多半是因为发生过相应的事故,结合酒店内各种劣质的设施来看,这个电梯一定是不咋可靠的——其实在我仅有的几次乘坐中就遇到了些小故障。而那个家伙徘徊在三楼和顶层、电梯与楼梯之间——说不定也打算半夜来看星星。另外,这酒店早年的背景非同凡响,在这杳无人烟的地方确有些不可言说的往事。
所以,我们尝试还原一下:多年以前,某个倒霉蛋在等电梯,但电梯出现故障,开门时并未到达指定的楼层,于是他掉到了电梯顶上,而后电梯冲顶,他的灵魂便留在了三楼和顶楼之间——至于楼道那边,大概是死亡也不能耽误他去看星星吧。当然,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理罢了,况且无论如何,这一切也同样不能耽误我去看星星,这是最重要的事,毕竟无论走到哪里,星空都是不变的,它永远为我指路,我岂能不永远去见它呢。
对了,但还有另一件怪事:如前所述,二楼的楼道有一部分是可以直接看到一楼大堂的,日落后酒店员工们都坐在大堂中各自玩手机,大概十几个人,包括那个前台女孩,但每当我走过时,他们都会抬头盯着我——每一个人,每一次,从我出现到离开——他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粘在我身上。第一次,我认为这是动物对突然出现的移动物体本能的好奇,第四次,我开始觉得有些怪异,第八次,我已经习以为常。不管怎么说,他们只是盯着看,也没说或做什么。
晚上十一点,楼顶已经可以看到银河了,我回房间叫妈妈上来看。我们先从左侧的楼梯上楼,再从天台走到右侧,因为左侧天台四周灯光太亮了。在穿过那片地形复杂的中间地带时,我听到许多声音,管道里的水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自言自语的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黑暗中,妈妈突然问道。
我问她指的是哪个声音,她说她不知道,又说好像是风声。这里非常黑,我不愿在黑暗中说话,从安全的角度上讲,在黑暗中应尽量保持安静,因为自己的声音会掩盖其他声音并暴露位置——走夜路时唱歌绝对是件危险的事——因此我想让她停下来,便附和着说:“就是风声。”
后来回到房间我问起她,她说她并没有听到脚步声和男人说话的声音。
但我听的非常清楚。
我又去看了酒店的评价,确实有人反映过在无人处莫名听到脚步声,而酒店的回应是地板因老化产生的声音。不知为何,妈妈听不到那些声音,但她却比我还要害怕,以至于刚刚凌晨十二点半,她便不愿我再独自去天台了。
当然,我最终还是成功上去了。多么美的银河,岂能因为一位失落的鬼魂就不去欣赏了?这次我没去右侧,左侧的灯光只是影响拍摄,但不影响我的眼睛,毕竟时间有限,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多走些路。我抬起头,感到心跳很快,这里很亮,楼道的灯光、村里的路灯、旁边酒店的招牌都照着这里,可我却切实地感到不安,我经常在旅游时独自跑到漆黑无人的地方看星空,却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我想他大概也喜欢站在那个位置看星星。我不想理他,继续在天空中寻找认识的星宿,仙后座、牛郎织女、北极星……直到一个冰冷的东西贴到了我的后背上。
我回过头,没什么可怕的,只是阁楼的外墙,但这说明我一直在无意识地向墙角倒退。我知道该放弃抵抗了,我走向了漆黑一片的右侧天台,这里如此宁静,我安心地躺下,几乎要融化在黑夜中——直到狗叫声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如果藏马熊在当晚并未出现,而我却因为害怕它们而没能去湖边欣赏夜景,我将会变成另一只幽怨的鬼魂。幸好,楼下的熊狗之战拯救了我。七八只藏獒围着保安亭狂叫,而阴影中是一个巨大的动物,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熊的叫声,和虎啸一样令人心脏不适,大概也是因为次声波。
我回到房间,翻到窗口上看着那条街道。我突然意识到,那里空无一人,却又站满了人,我看到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为何在这里。当然这没什么稀奇的,这世界上本就充满了鬼魂,拥有相似经历的人们死后也喜欢成群结队,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之间似乎不全都互相认识……这真是我见过最混乱的场面。
我知道藏马熊有一些糟糕的习性,比如活吃猎物,而且在这附近确实发生过吃人事件,但其他那些人呢?爸爸喜欢藏地的历史,他告诉我,中象雄文明的祭祀相当血腥,不乏活祭、用人的尸块做法阵之类的仪式。我想,他们来自那么久远的过去,怪不得与这些后来者玩不到一起,不过我竟有幸见到了他们。我还想再看一会儿,但是该睡觉了,妈妈已经要生气了。
翌日,太阳照常升起,我也照例赶在最后一分钟去餐厅吃早餐,当惹雍错依旧美丽而沉默,我和它挥手告别。随后的上午似乎所有人都没什么精神,我将安静的三个小时当作献给圣湖的回礼。
我曾偶然获得一颗狼牙,一直悉心保养,贴身戴在胸口,我以为它会陪我一辈子,可是离开文布南村后,我发现它裂开了。我又告诫自己不应恋物,毕竟所有具体的物品都会消失。我从一个藏族老奶奶那里买到了一条相当古老的尸陀林手串,在一堆美丽而崭新的牛骨饰品中我一眼便看中了它,我的眼睛看到它的力量,我的手却感受不到。尸陀林主意在提醒人们“无常”,但我自知——至少对有些事物——我不愿接受无常……起码给我相对的永恒吧?相对于人类短暂的生命。
我的小狼牙裂了,我为它流了眼泪,人们都说护身符裂了就没用了,它却仍能给我力量。我走进西藏的每一座寺庙,跟着信众们跪拜,就像在欧洲时在教堂中祷告。我扪心自问,既然不是信徒,为何四处求神拜佛,难道只是喜欢凑热闹?直到今天突然转过身才看到,我在向自己祷告。
为了纪念小狼牙,我决定暂时同意接受“无常”,可这时我却又突然有了无穷的力量去爱所有短暂易逝的事物,我从未如此确信我可以爱他们。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明白了一件事为何不可做,便又会突然知道它是可做的。这是否是因为我总是过早地下定论?其实不能怪我,也许本就没有什么规律是永恒不变的——当然,变化应是个例外。